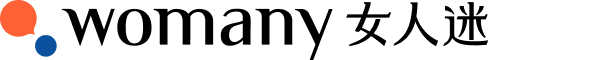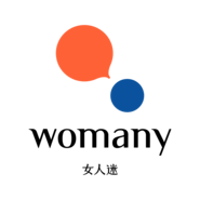文|Womany Abby
青春惑亂迷走,如果有那麼一本書,讓我放在手心沈澱澱地便安心,知道憂傷痛苦都是可以被理解的,那是《其後》。
我先讀《其後》才讀了《蒙馬特遺書》,但是先遇見誰都不影響文學,那些被藝術萃取的靈魂,看著那麼醉人,走近才嗅見他們苦的回甘。
在作者圈裡,她報導講座鮮少、異常低調沈默,賴香吟說討論就還給文學。她不是從小就在寫字的人,寫字疏離有時、近的讓人筋疲力盡也當然。從台大經濟系到日本文化研究碩士,兜兜轉轉還是回到了文學這條路。從《其後》到《文青之死》,賴香吟走出個人經驗觀看時代。
我一直以為賴香吟像慢版的英搖,悲壯的緩而激情。她走進來時我放著 Elliot Smith 的《say yes》,但她苦著臉說,我其實是因為要寫這短篇才聽搖滾樂的。
推薦閱讀:從佩蒂史密斯到小野洋子,搖滾樂的靈魂愛侶

《文青之死》中最後短篇與書同名,賴香吟說:「〈文青之死〉寫給你們這一代,我希望你們不要陣亡。」
文青之死:當理想幻滅後,你還剩什麼可以堅持
〈文青之死〉用搖滾樂做背景音,她說搖滾樂的精神是 Fight 、敢於吶喊的奮鬥。可她不似搖滾,聽著錄音檔時更像古典,一樣的音階,一層、一層堆疊出故事。你初見整潔明亮,每一個字與字間都乾淨地沒有罣礙;直到深隧悲傷,她讓時代的軸拉遠拉長就像悲壯史詩。談起這本書的起點她說:「這本書就是在當今千瘡百孔的社會結構下,看見這個世代(三十歲至四十歲)所經歷的家庭、職業。」
《文青之死》寫給解嚴後一代:「1987 解嚴後,有些人走過九零與一零,小說設定在 2012 年總共 25 年,這 25 年是人一生變化最大的階段。世代是《文青之死》的重要命題,談每一輩的懷有理想的人:「文青現在是比較輕鬆的說法,我談的是老文青,解嚴後到現在所成長的這一批人。台灣解嚴至今社會變動很大,如果你是跟隨解嚴一路成長來的人,面向婚姻家庭職業、正卡在社會結構劇烈變化的時空。曾經有過很多希望,出現很多變革,接下來出現很多問題,現在在收爛攤子。」
推薦閱讀:運味:我們如此飢餓,對於理想這麼渴望
20 到 45 歲記錄一個人從青春成長到成熟的黃金時期:「這個過程是追尋、實踐、幻滅。我們在個人追尋,政治也一樣,從談自由民主到轉型正義,在我來看整個大結構也是追尋、實踐到幻滅。」
賴香吟寫實時空,看得見社會生產的議題,性別與族群、房價與生存、民主與自由。我請賴香吟談談幻滅:「你訪綱裡有一句我覺得就是這樣:死而後活、離後懂愛。我說幻滅不是絕望,而是看清問題所在。經歷幻滅,我覺得就是再出發跟再堅持了。你不需要追尋,人生沒有時間,就是再堅持了。」
當理想幻滅後,你還剩什麼可以堅持?從那些碎片裡撿拾最後不願棄守的價值,就是再堅持。
「在你生命腐壞之前,在黑暗重新點一盞火給自己。人經過挫折幻滅,如果你還想再走,你得再堅持,人生要心甘情願。」
你若還在衝撞,但願你少受點理想的皮肉傷;你若泯滅理想,願你還留有一絲真。反覆咀嚼 Fight 這個字,人生,何其有幸能為自己戰鬥一次。
婚姻家庭,為何比不上知識愛情?
在文本裡賴香吟提出對婚姻與家庭的質疑,她質疑的不是婚姻制度,而是不適合的婚姻:「當我們書寫各種不適合的婚姻故事時,我們要改變的不是婚姻制度,而是『不適合』。因為價值、刻板印象造就不合適的婚姻。」
同場加映:【中國性別觀察】信者得愛,一生只送一人鮮花的浪漫?
「相對於知識愛情跑在前面,落後的是結構。」
故事裡有離婚後無法爭取養育權的母親、一生為婚姻奉獻的女人、有企盼失格失序的妻子。這些女性形象並不疏離,她們不離經叛道、不獨立不進步,是一個個真實活著的身影。賴香吟看女性多半必須在家庭與自我間做比例性的抉擇:「對我們這代來說,女性應該追尋自我、跟外邊的體制爭取。在談性別議題時,知識與愛情是個正選項,你可以通過知識強化自己、認識女性主體、愛情更明白是個自我創造
知識與愛情可以透過個人實踐,婚姻家庭卻必須與體制交戰:「
知識愛情升級,但在社會結構與家庭制度上,卻沒有相對應的調整:
我們談獨立女性形象時,是不是遺棄了女性在現實生活裡避不開的困
推薦你看:「剩女」的生存法則:經濟不獨立,可以嗎?
「婚姻家庭被知性蒸發掉、被避而不談。但我們確實在經歷這樣的人生,逃不掉的。」
寫作先去除浪漫幻想,就是沒辦法才寫
我請賴香吟從《文青之死》談談「寫」之於她:「我想是給同世代留下記憶,用你我都經過的人生,寫一個故事。指出現象以外,還要把社會鋪在後面,這是文學的責任。精準把故事背後盡量具體而微的提示出來,讓故事可以投射出更大的景深。你隱約知道這不是故事兩三個人的問題,你會嘗試看見景深的東西。」
不斷去尋找問題跟解答,自我認識生命,是她身為創作者的己任。賴香吟說藝術是不能折合新台幣的,藝術是勞動業,像農夫也像工匠,充滿苦澀孤獨:「為什麼我們甘於其中,一定有點價值的,雖然只是個人價值。我希望任何對藝術創作有興趣的人,要知道它很折磨,去掉對藝術浪漫的幻想。」
賴香吟沒想過寫作會是人生,開始寫與浪漫無關:「對我來說,
寫作是一種沒辦法,讓人頭疼得無可奈何,卻也甘願的篤定。賴香吟說寫作是有時差的,作品正在跟社會對話,我已經跑到後面了,寫作者,像是一路拋棄作品似的:「寫作真是件孤獨的事,你只能一個人,跟當下搏鬥。我們談一本書,都像是退伍老兵在談結束的戰役。」
給橫衝直撞的靈魂,生命要能減速
《文青之死》也如一場場人生戰役,像是站在荒蠻漫天黃沙間,塵土裡都還有歷史的血跡、還有死去之人尚未被超渡的魂。於是,賴香吟用 Slow Down 這個字,給還魂的理想:「Slow Down 這個字,是給那些價值比時代更前面的人,他們性格纖細靈敏而劇烈,無法容忍一點點謊言或虛偽。所以這世界很矛盾的,我們都說人要真心,可是一旦真,在世界上是活不下去的。我們都學會保護自己、放棄一些價值,這是活著的姿態。有些人激烈反彈、衝得太快,這樣的人難以在人生中倖存,我說的減速,希望對這種生命體說,我只希望你減速,在快要爆裂前緩下來,別一頭撞上了。」
別一頭撞上了,在懸崖前還得勒馬,是賴香吟給世代的盼望跟祝福。「既要留存這個東西,又要跟它共處。」這個東西她沒有直指,我只能故作聰明地想,大抵是無以名狀了理想、看盡了現實後的理想。
《文青之死》在賴香吟生命減速下寫出來,她說自己也有過於靈敏的時候,書內的短篇錯落在許多時光裡,在那些慢下腳步的時候,細膩看見的社會:「減速完就要加速,寫太慢啦。」賴香吟笑著說,我都敢叫大家要 Fight 了,自己不加速不行的。
我用美好的字,寫最粗礪的事實
賴香吟經常話到喉嚨又吞回去。像是有什麼沒說明,又好像都說白了。就是:「對對,就是這樣。」的回應。
她對每個題目都很莊重、認真琢磨良久,我想她是對自己的每句話都特別嚴謹的人。我問起愛,她說《文青之死》談的是不愛:「沒有忠於自我、社會結構卡死你、情感暴力、沒有找到愛的對象,裡面是不愛的狀態。這是一本赤裸醜陋而不美的現實,我盡量把文字寫的美,因為內容像粗礪的石子,踩上去很痛。」美好的字成了刻意,像是在發炎的傷口後塗抹上鬆軟藥膏。

「雖然寫不愛,但每個人追尋的仍然是愛。
賴香吟說,我沒有這樣清楚說過:
理想幻滅後的最後一抹乾淨
小說最末,用《心靈捕手》最終幕的車,召喚世代記憶;有 Elliot Smith、Kurt Cobain 悼念流亡的靈魂;有 Allen Ginsberg、2046 勾引哀戚。
「如果你是吸收這些養分長大的人,你對人生浪漫幻想,你看著愛在三部曲(《愛在午夜希臘時》、《愛在黎明破曉時》、《愛在日落巴黎時》)長大,這個故事想找回文青最初乾淨的成分。我們的追尋、理想不該一筆勾銷,接下來可能也不會多好,就是一個老了的人生,但是還是要繼續。」
推薦閱讀:愛的永恆之道《愛在午夜希臘時》(Before Midnight)
四五六年級生青春的憤怒,都在這裡,與一個個死去的魂,沈到最底。
“I saw the best minds of my generation destroyed by madness, starving hysterical naked.”-”Howl” by Allen Ginsberg
我覺得她是沈著處理許多時空悲哀的人,那些社會留下來的垃圾、前人忘記帶走的遺物、結構生產的病兆,都佇立在小說背景。如她說的,是那些景深,生成了人物。而我們身而為人的悲哀,不是處事的難,是對生命的漠視。
文學家再疏離的處理題材,都還能看見白紙黑字間有人的氣味在鼓譟,灼燒著讀字人的五官。看著我們島嶼來時的路,看著我們即將走向的道。面向那些問題,賴香吟說還能怎麼辦呢,我們就是得面對。她話說的灑脫,沒有我對文學家浪漫幻想的甜膩,可是那些鏗鏘字句裡,潛台詞,都是愛。